私底下很害羞,是个典型的i人(内向者),哪怕走进只有3、4人的小房间,心率也会立刻飙升。
然而,一旦遇到自己的专业领域,例如,在数千人面前进行一场与睡眠相关的TED演讲,他的心率却可以平稳到每分钟40几,用他自己的话说,“那是我最放松、最真实的时刻。比人生中任何其他时刻都更像我自己……我不太愿意说是‘自信’,但我确实很自在。”
这就是Matthew Walker(马修·沃克)。
——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神经科学与心理学教授,同时也是该校人类睡眠科学中心的创始人。
由Steven Bartlett(史蒂文·巴特利特)制作并担任主持人的著名博客系列「CEO 日记」,在2023年3月采访了Matthew Walker。
透过采访,你将了解到:
- 睡眠的各种有趣小科普;
- 咖啡因对睡眠的影响(Matthew是支持喝咖啡的!);
- NASA级别的小睡(午休)策略;
- 谷歌小睡舱:重视员工睡眠如何带来职场的高效、公司的利润;
- 安眠药、天然睡眠补剂的真相;
- Matthew本人的助眠Tips。

Matthew Walker
Steven Bartlett:有人说,资本正在侵蚀我们的睡眠?你如何看待这个说法?
Matthew Walker:几年前, Netflix 的 CEO (如果我记错了,请在评论区纠正我)曾公开表示,“我们决定向睡眠开战”。我简直震惊,ta们把它当成战略目标来宣告。
可见,从资本的角度,社会希望我们要么在生产,要么在消费,而在万籁俱寂的睡梦中,你既不生产也不消费。
Steven Bartlett:假如说,你有权力去设计一套所谓的“睡眠规则”,让全世界的人遵守。你当前最想从哪些方面着手?
Matthew Walker:啊,这个问题真好。
我有过类似的畅想:例如,宏观上,国家如何把公共健康宣传做好。因为,独立调查机构兰德(Rand)曾发布一项数据报告,内容是,睡眠不足会让国家遭受约2%的GDP损失。在美国,这是 4110 亿美元的利润损失,在英国是 500 亿美元。
微观上,在职场里,这样的偏见无处不在:睡眠/休憩是弱者的专利,觉少则是硬汉和高效人士的勋章。
但,你知道吗?睡眠是我们所能获得的最顶级的“生理风险投资”。如果 CEO 开始重视员工的睡眠,公司将更高效,更有生产力,利润和收入也会增加。
Steven Bartlett:Wow。有案例或数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吗?
Matthew Walker:NASA(美国航空航天局) 在1980 年代做过一个研究,当时,ta们正在考虑给宇航员安排小睡。原因是,当你在太空绕地球飞行,根据轨道不同,24 小时内能看到大概 10 到 15 次日出。听上去很壮观很奇妙,但相信我,对睡眠来说却是彻底的干扰。
于是NASA开始研究如何战略性地利用小睡来提升宇航员的表现。要知道,太空探索里最薄弱的一环其实就是人类自身,而人类的失误分分钟带来灾难性的后果。
那么,NASA的发现是,只要小睡 20 分钟到 1 小时,宇航员执行任务的效率就能提升大约 34%,整体警觉度则提高了50%以上。
这些数据太有说服力了,以至于被大力推广,形成了所谓的 “NASA 小睡文化”。举个例子, 谷歌园区里就有专门的小睡舱。

Matthew Walker:这些大公司之所以鼓励员工休息,绝不是因为对人类的健康、福祉多么富有同理心,而是,ta们深谙效率就是金钱,而睡眠能换来效率。
反之,为什么我们说缺觉等于低效呢?有数据和实验支持:第一,当员工睡眠不足,ta们会倾向于选择更简单的杂务。打个比方,处理邮件、听语音留言,而不是专注在那些需要深度思考的项目。
第二,即便专注了,产出创意方案的概率也更少。
第三,我们发现,在执行团队任务时,缺觉的人往往更容易摸鱼。结果便是,ta们搭上了别人辛苦劳动的便车,却破坏了公司里本该有的信任氛围。
最后一点很有意思——作为公司高层,你的人格魅力关乎着你对团队的有效激励能力。而睡眠状况会直接影响这一项。实验让员工给领导者打分。结果显示:当你睡眠不足,你的得分就是会低,员工的普遍感受是,CEO今天没那么有魅力。
(「弥尔顿说」:其实很好理解,睡眠不足的上司很容易脾气暴躁、冲下属发无名火。或者,由于状态不佳,在一些重大决策上没那么有说服力。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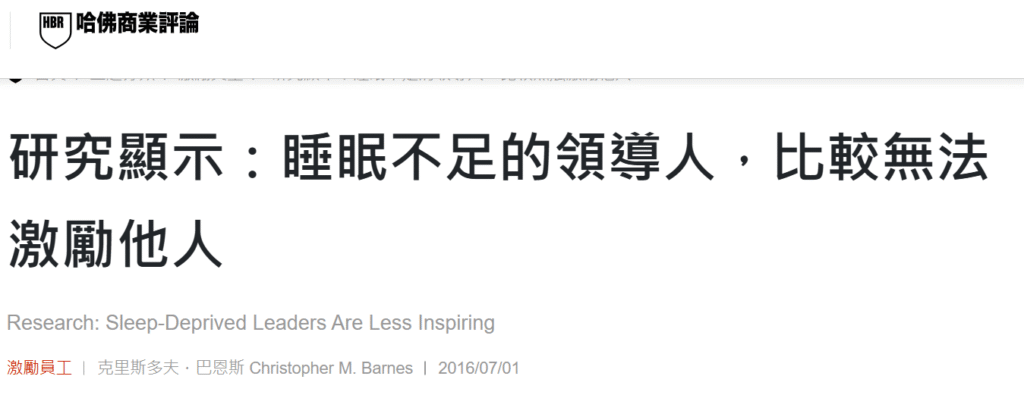
Steven Bartlett:我一直拒绝“小睡”、“午休”。尤其当我知道有“睡眠周期”这一回事之后,专家在此,你能为我们科普一下吗?
Matthew Walker:是这样的:前 10 到 15 分钟是浅睡眠,接着是深度睡眠,大概在30到40分钟。然后,你会再次回到浅睡,直至进入短暂的REM睡眠。这整个周期——从非快速眼动到快速眼动睡眠,平均大约 90 分钟。接下来,便又是从浅睡开始,如此循环往复。
*快速眼动睡眠,英文是Rapid eye movement sleep,故称REM睡眠。
REM 睡眠是大多数梦境发生的阶段。此时,你的心率、血压、大脑活动和呼吸都会升高。尽管眼睛是闭着的,但会快速转动。而你的手脚肌肉会暂时失去活动能力,从而防止你在床上做出梦里的动作。
Steven Bartlett:90分钟……所以我会认为,15 到 20 分钟不是没有意义吗?根本不够我进入深度睡眠……
Matthew Walker:这不是你一个人的困惑。我有时还会被问,怎样才能获得更多的 REM 或深度睡眠?人们总觉得那才是“最好的部分”。
但事实是,睡眠的不同阶段各有它的功能。除了那种太浅的非快速眼动睡眠(我们通常不希望它占太多),几乎没有所谓的“坏睡眠”。
我和同事做了很多研究,我们发现,即便只有短短的时长,你也能从小睡/午休中获益。它是全方位的:提升学习和记忆力、改善心血管健康,甚至于调节情绪,比方说,降低焦虑、让你不容易陷入负面思维。
然而,小睡虽好,却不能贪多。20 分钟就够了。有一项研究把时间缩短到大约 9 分钟,结果发现人的警觉性和反应速度仍然有一定改善。如果你是运动员,这就很有意义了。
所以,尽量控制在 20 分钟,一旦超过,你很可能会进入深度非快速眼动睡眠。当你在深睡阶段被闹钟吵醒,你会感觉非常难受,像宿醉一样。
这是因为,你不是从浅睡眠或 REM 睡眠中醒来的,这两种才是我们一般说的“自然醒”。
但有一种情况是不建议白天小睡/补觉的,就是你有失眠或其它睡眠障碍。
底层逻辑是,当我们醒着时,大脑会分泌一种叫“腺苷”的、让人有睡意的物质。醒得越久,腺苷就累积得越多。而睡眠能让大脑清除这些物质。
对失眠的人来说,白天补觉犹如给高压锅开个小孔,把本该留给夜晚的“好困意”提前释放掉了。
此外,即便你晚上睡得不错,也尽量不要在下午 2、3 点之后午睡。这和正餐前莫吃零食是一个道理,为的是不让你失去睡眠的“好胃口”。

Steven Bartlett:你对咖啡因的态度是?
Matthew Walker:我是支持喝咖啡的。稍后我会讲为什么。
但在此之前,我希望大家能知道,咖啡因会以至少3种方式扰乱你的睡眠:
首先,咖啡因的半衰期大约是5到6个小时,这是什么概念呢?——我们的身体需要5到6个小时来代谢掉一半的咖啡因。这意味着,10到12个小时后,你体内仍残留有1/4。
换言之,如果你中午喝咖啡,到午夜时,你只代谢了3/4。夸张一点说,这几乎等于你临睡前炫了1/4杯咖啡。
其二,咖啡因之所以提神,离不开我们刚刚提到的“腺苷”。
举个例子,你想熬夜肝新项目的提案,但现在是晚上10点,你的大脑不断接收到腺苷的信号,让你觉得睡意朦胧。
于是,你喝了杯意式浓缩。然后,发生了什么?——腺苷的信号被阻断了,因为咖啡因涌入大脑,它开始“鸠占鹊巢”,迅速抢占腺苷受体。
一时间,睡意不见了。
但问题是,腺苷不会就此消失,它只是被粗暴地驱赶到一边。随着时间的流逝,体内游离的腺苷只会越来越多。
因此,当咖啡因被代谢之后,你不仅会回到几小时前的困倦状态,还会被这段时间里不断积累的额外困意一并“击倒”。
这就是所谓的“咖啡因崩溃”。
其三,它会削减你的深度睡眠。我们在实验中发现:100–200 毫克咖啡因(大约一杯半)会让你的深睡减少约 15%到30%。
曾有人对我说,“我是那种晚餐后喝两杯浓咖啡还能一觉到天亮的体质。我睡得很好,咖啡对我没有影响。”
问题在于,当你入睡,你是意识不到自己错过了深度睡眠的。但你会慢慢发现,一杯咖啡不“管用”了,要喝两杯、甚至三杯,这正是你没有获得足够的修复性睡眠所致。而充足的深睡本该让你精神充沛地醒来。
Steven Bartlett:但你仍然支持喝咖啡?
Matthew Walker:是的。
我很喜欢清晨现磨咖啡的香气,还有那个仪式感。此外,在适度范围内,生活总得有点乐趣,除非你想成为墓地里最健康的人(笑)。
实际上,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,喝咖啡对身体有好处。原因很简单,咖啡豆本身含有大量的抗氧化物质,例如氯原酸(chlorogenic acid)。而现代饮食往往缺少了这些重要的抗氧化成分。
然而,这种“好”并不是线性递增的。不是说,你喝得越多越健康。它的效果大约在两到三杯时达到峰值,然后就开始递减。
一句话,剂量和时间决定了它是否成为“毒药”。
顺便告诉你,我喝的是脱因咖啡(decaf),倒不是说我想成为睡眠“冠军”,而是我属于咖啡因代谢慢型。大家可以去做一下基因检测,了解自己的代谢速度。

Steven Bartlett:安眠药呢?我有朋友用它来助眠,还说自己买的是“纯天然”品牌。也许是刻板印象吧,我总觉得,“是药三分毒。”
Matthew Walker:在回答问题之前,我有必要说一声,我不是执业医生,我仅在此分享科学事实,请不要把它们当作医学上的处方。
那么,我要说的是,2016年,美国内科医师协会(ACP)集结了一个专家小组,用于调查关于经典安眠药的大量文献。然后,ta们的建议是,安眠药不应再作为治疗失眠的首选,必须优先采用的是认知行为疗法(CBT-I)。
要理解这一点,便需要了解:
安眠药属于我们称之为“镇静催眠药”的类别,而镇静不等于睡眠。在极少数特定人群里,所谓的“睡眠补充剂”也许会有一点作用。但从更系统的研究来看,它们的有效性并没有被证实。
想想看,如果真有这么一种纯天然的补剂,对睡眠有奇效,那全球睡眠障碍人数应该早就锐减了,也不至于成为一个普遍的议题。
在ACP的专家小组看来,安眠药的益处“微小且临床意义存疑”。尽管在临床医学中,安眠药确有它适用的时间和场合,但它一般是作为认知行为疗法(CBT-I)的辅助,被建议短期使用几周,但大多数人却使用了几个月甚至几年,这就是问题所在。
Steven Bartlett:假设我是一个失眠的人,认知行为疗法能为我做什么呢?
Matthew Walker:我们会和你一起,关注你对于睡眠的想法、信念。举个例子,我们会询问,“卧室是否令你感到焦虑?”
对很多失眠的人来说,卧室如同战场,你看着床,内心发怵,“今晚别又睡不好。”
还有一种是,半夜醒来,却再也无法入睡。
Steven Bartlett:那该怎么办呢?比方说,眼下是凌晨3:23了,我必须在7点起床,赶飞机什么的,那就只剩不到4个小时可以睡。
Matthew Walker:别去盯时间。
很多人会忍不住看手机,想知道几点了。但知道现在是几点,而你既没有睡着,还有一个出差要赶,只会让你更焦虑。
标准的建议是,如果醒来30分钟后还睡不着,那就起床、离开房间。
不要刷手机。你可以拉伸、冥想、读书或者听播客。也不要吃东西,因为大脑对“奖赏”特别敏感,而一旦建立“醒来=有食物”的强联系,你会更容易在半夜醒来。
为什么是30分钟呢?——你在床上待的越久,你的大脑越容易把“床”(物体)和“醒着”(行为)联系起来,然后通过行为的重复形成一个认知,叫“床是一个我永远睡不着的地方”。

Matthew Walker:所以我们需要打破它。方法就是离开你的床,然后,等你困了再回去。时间上没有限制。这是为了训练大脑重新习得:床是睡眠与休憩的所在。
然而,很多人压根不想下床,尤其在大冬天。
那么,这就来到了一个我曾不以为然的东西:冥想。它一度让我联想到大家手牵手唱圣歌的情景,于是我想,太玄乎了,不适合我。
直到,研究一次次把我引向冥想对失眠的改善。那些数据太有力了。
所以我开始睡前冥想,每次10分钟,已经坚持了四年。即使在半夜醒来,我也会尝试通过冥想来调整自己。
Steven Bartlett:你提到了听播客。
我是属于边听边入睡的。然后呢,这让我的另一半挺头疼的,因为我偏爱罪案内容,例如连环杀手,总之是那种能彻底抓住我注意力的,我才能沉浸进去。而我的伴侣正好相反,她喜欢安静。
你说,我怎么就喜欢听连环杀手呢?
Matthew Walker:这里可以聊的东西太多了,有心理学,有体质、神经系统的各异性。
但我仍想从“冥想”的角度去切入。有个很值得一提的冥想类App,叫Calm,曾陷入经营危机。而拯救它的,是“睡前故事”。
小时候,有父母念童话书伴你入眠。成年后,这个需求并没有消失。证据就是,Calm在其App里加入了“睡前故事”,公司估值因此飙升到10亿美元,成为行业独角兽。
睡不着时,我们很容易开始胡思乱想:今天做了什么?哪句话接得不好?天啊,明天还有一堆事……忽然间,你完全清醒了。
而无论是冥想,还是听播客/晚安故事,它们的作用本质上是相通的,那就是——把注意力从自我身上抽离。
和它类似的建议是,在脑子里带自己“散个步”。
我的这位同事,阿利森·哈维 (Allison Harvey),她的另一个发现是,当你闭上眼睛,想象一条自己熟悉的路,然后在脑海里尽量细致地还原,例如,和狗散步的路线——走出家门,左转下台阶,然后沿着街道走,遇到第一个路口再左转,经过那棵松树……类似这种细节程度。如此在脑子里“走”一遍,入睡的时间能缩短约50%。
Steven Bartlett:我听过 Calm 的睡前故事,“冰冷潮湿的窗台上,雨滴啪嗒、啪嗒地敲打着……”它会有这种细节描写,和我听连环杀手从窗户潜入其实挺像的。
Matthew Walker:对对对!
Steven Bartlett:它就是能令你昏昏欲睡。这是为什么?
Matthew Walker:就像 “带宽” 一样,人类的认知容量是有限的。
如果你的注意力被这种细节占满了,也就没有空间让焦虑、担忧跑进来了。
然后,如果你既不想听播客、也不想下床,我能给出的终极贴士就是,彻底接受“睡不着”这件事。
现实是,每个人都会有睡不好的时候。就我本人而言,至少有过两段顶严重的失眠经历。
与其强迫自己努力入睡,不如告诉自己,“好吧,我就躺着休息、不必睡着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