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月3日,英国企业家Steven Bartlett(史蒂文·巴特利特)在他的油管频道《CEO日记》采访了Anna Machin(安娜·梅钦)。
Anna Machin是一位进化人类学家,也是两个女儿的妈妈,任职于牛津大学实验心理学系。
对话从大脑与激素、人文与心理的角度切入,涉及了育儿、父职、恋爱、亲密关系……
此篇编辑、翻译了育儿、父职相关内容,废话不多说,直接上访谈。

Anna Machin
Steven Bartlett:到目前为止,你一直在为哪件事倾注自己的人生?
Anna Machin:这20年来,我的课题围绕着「爱与亲密关系」。
我是人类学家,而在我看来,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核心。
如果把外在的一切都剥去,只剩食物和水,那么接下来你最需要的,是关系,是爱。
我们这个物种很幸运,能够以很细腻、很丰富的方式去体验爱。而这也会从根本上影响一个人的寿命、健康和幸福感。所以我觉得,随着技术和AI不断涌入生活、节奏越来越快的当下,我们更需要回到那个最本质的问题:
我们到底是谁?
爱,又究竟是什么?
因为——你如何去爱、你爱谁、你怎么看待爱,基本上就构成了「你是谁」。
Steven Bartlett:你刚才提到“人类学家”,能解释一下那是什么吗?
Anna Machin:当然。人类学家是研究人类这个物种的人。
我是一名进化人类学家。这意味着我偏向科学那一边(人类学有的更偏文化方向,有的偏科学)。
我研究的是进化如何塑造了我们,为什么某些特质会被进化出来,以及,爱是如何演化来的?父亲的角色是怎么形成的?我会通过基因学、扫描技术等等来找寻答案。
Steven Bartlett:我眼前就有两本你写的书,一本关于“爱”,另一本是关于“父亲”的。而你本人也非常擅长聊“父职”。
我的问题是,是什么让你把这两者联系到了一起?
Anna Machin:因为我有了小朋友。
像大多数准父母那样,我和另一半提前讨论过,决定开始备孕。后来怀上了,很开心,一起测的验孕棒,一起上产前课程,一起去做B超,一切都很好……
直到生孩子那天,我失血过多,女儿刚出来时状况也不太好。事后医院给我安排了各种心理疏导,问我要不要谈谈。
但说实话,我觉得自己还行——因为我中途晕过去了,什么都不记得。
可我老公在旁边目睹了整个过程。
他等于是眼睁睁看着一场慢动作的车祸,车里是两个他最深爱的人。我完全能理解那对他来说是怎样巨大的精神冲击。
但没人告诉他到底发生了什么。
ta们把我收拾好,把宝宝带去新生儿重症监护室,然后就把他一个人留在产房。我当时呼吸微弱,他吓坏了。
此后的整整两年,他都没法谈论那场分娩,也没法处理这个经历带来的情绪。他甚至很担心再要一个孩子。
这让我很生气。
我的点在于,我丈夫,这个对我而言极其重要、选择在场亲历我们小生命诞生的人,为什么却被当作局外人一样,被彻底忽视了?
随着我们的女儿一点点长大,我更是亲眼见证了这份重要——从他和女儿与日俱增的羁绊,到如今ta们完全融入了彼此的生命。

Anna Machin:于是,回到牛津时,我心想,作为人类学家,有必要做个调研:我们社会对于“父亲”究竟了解多少?
结果,有大量研究聚焦在“缺席的父亲(absent fathers)”这一块。我的意思是,那些不尽责、让另一半陷入丧偶式育儿的人固然是大问题。但,那些无论是否同住、始终参与到孩子成长中的爸爸,却几乎没被提及。
所以,我就从最基础的开始问起:
- 一个男人成为父亲之后,会发生什么变化?
- 他在生理上、心理上会有什么转变?
- 他是怎么和孩子建立起关系的?
- 这种关系的本质是什么?
-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,他有没有一种不同于母亲的角色?
然后我招募了第一批人——15位新晋奶爸。当时他们的伴侣刚怀孕三个月。
这就是20年前我研究的起点。
Steven Bartlett:我此刻最好奇的是,从什么时候开始、因为什么,才让爸爸们在“育儿”这件事上那么不受重视?
Anna Machin:这和文化规训有关。你比如说,在我们的文化里,从维多利亚时代延续下来的,就是一个负责立威、惩戒和赚钱养家的单一的父亲模板。也跟我们长期以来的社会政治制度有关,例如,女性长时间被限制不能外出工作——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非常近代。
但这些观念背后并没有任何生物学依据,完全是文化造就。
无奈的是,它们太深入人心了。爸爸们总是被描绘成缺席、没用、笨手笨脚的样子,举个例子,《小猪佩奇》里就是一个典型的笨爸爸。
而实际上,世界各地都有那种亲力亲为的爸爸。刚果的阿卡部落就是其中之一。狩猎采集时,爸爸是那个背着孩子穿越丛林的人。他们会给孩子唱歌、讲故事,所以娃都是跟爸爸而不是妈妈睡。甚至——这总是成新闻头条——他们会用自己的乳头安抚哭闹的婴儿,直到妈妈准备好哺乳。
Steven Bartlett:我采访过Erica Komisar,她认为,妈妈在孩子刚出生的前两年更重要,而从孩子大约两岁、开始进入玩耍期后,爸爸的作用才变得关键。
Anna Machin:我会在这一点上反对她。
几天前,我在一个活动上遇到一位男士,他是一名社区工作者,主要负责与爸爸们打交道,支持他们、提供帮助。
聊着聊着,我才知道他家里也有小宝宝,才六个月大,我就说“恭喜你呀!”。他说:“谢啦,不过我知道自己现在其实没那么重要,至少要等宝宝18个月或两岁以后吧。现在我就只是换换尿布而已,也帮不上什么大忙。”
我当时心想,天哪,这话出自一个专门做父职教育的人……我就告诉他:“不不不。从宝宝出生的那一刻起,你就是非常重要的。”
Steven Bartlett:为什么呢?
Anna Machin:这关乎到宝宝大脑的发育。
要理解这一点,就得展开讲讲——其实,人类都是“早产儿”,本该在子宫里再待上几个月,但我们每个人都提前降生了……
之所以会这样,和人体构造的两个特点有关。
第一,我们的脑子实在太大了。一个发育成熟的人脑要比同体重的哺乳动物大上六倍。这上面有那么多皱褶,层层叠叠的,为什么?因为我们得把这么大的脑子塞进头骨里。
第二,我们是两脚兽。如果你观察黑猩猩,它们以四肢行走为主,腿分得很开,所以它们的产道很宽。而人类的产道非常窄——我们为了保持直立行走,骨盆变得更紧凑。所以,人如果像其他猿类一样,在婴儿的大脑快发育完全的时候才分娩,妈妈和宝宝都会面临生命危险,人类很可能早就灭绝了。
大约在180万年前,人类进化出了这种“提前出生”的策略。正因如此,人类幼儿出生时才显得特别无助,不像黑猩猩的宝宝,它们能自己动、能抓牢东西。

Anna Machin:而没来得及在子宫里长好的大脑,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进入一个飞速发育的阶段——尤其是前额叶皮层,也就是掌管社交的区域。在这块脑区里,爸爸的作用尤其关键。所以从宝宝一出生,爸爸就必须参与进来,给予关爱和刺激。妈妈当然也非常重要,但必须是两个人一起参与,或者至少要有类似的支持,宝宝才能健康成长。
那些认为“爸爸只有在孩子两岁之后才重要”的人,抱歉,你们对大脑发育和儿童发展有着根本的误解。
实际上,你得尽早开始和宝宝互动,ta需要你的触摸、你的气味、你的声音——这些感官的输入来刺激大脑的发育。
当然,我们看到,这个时期妈妈往往参与得更多。部分原因是,负责孕育和哺乳的都是女性,在生理上她是唯一能做这件事的人。所以从这个角度,她是被“绑定”的。
但是,宝宝的成长环境并不只是「谁在照顾、谁在抱ta」。我一直都会跟准父母讲一件事:你们两个人的关系,也在无形中构建了这个环境。父母之间的互动,婴儿也会吸收、感受到。
所以,我也一直在努力推动这件事情:把「育儿关系」纳入产前课程。因为,爸爸妈妈有各自的育儿观念、特点和风格是很正常的。你们会有分歧、会争吵——但吵架从来不是问题,如何和解才是问题。关键是要找到属于你们的、良性的冲突处理模式。
Steven Bartlett:我自己也快到为人父母的阶段了。我和我妻子都有各自的事业。所以我在想,当我们的小生命出生时,怎样分工才是最理想的?
Anna Machin:嗯……这真的要看:什么对你们来说最可行。每个人的处境都不一样。准爸妈真的特别容易陷入自责,但我想告诉ta们:快乐的父母才能养出快乐的宝宝。
没错,婴儿有各种需求,但ta们也需要一个各方面都健康的养育者。所以真的,不管你们怎么安排,只有适合你们的才是好的。
Steven Bartlett:我比较幸运,工作时间更灵活。所以我是可以做出调整的。
Anna Machin:那么你可以试着多陪陪宝宝,实打实地做一些照顾ta的事。
当爸爸这件事,对多数职场男性来说,大概需要两年时间去完全地适应。而女性到妈妈只需要九个月。
为什么?因为你适应和认同这个身份的速度,取决于你作为父母的「能力感」——你觉得自己有多胜任。
也就是说,那些有机会照顾宝宝的爸爸,转变、适应得更快,因为他们越来越上手,这种胜任感会加速他对父亲这个身份的认同。
Steven Bartlett:这种转变是生物学上的变化吗?
Anna Machin:有生物学的——例如大脑和激素的变化,但更多的是心理上的,你要调整你的身份认同,把父亲这个新角色融入自我认知,并且感到舒适。而难以适应这个转变的男性,更容易出现产后抑郁。
你的伴侣有先天优势,因为她会经历怀孕和分娩,所以常有新手爸爸跟我说:“我也想参与。但就是找不到「时机」。”
我的建议是——做点特别的、只属于你和小宝宝的事情,比如,洗澡的时光归你,又或者,给ta们讲故事、读绘本——这永远不会太早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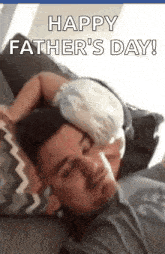
Anna Machin:还有一个特别好的——给宝宝按摩。新生儿的视力较差,但嗅觉非常灵敏,此时ta们无异于对感官刺激特别敏感的小哺乳动物。所以如果你给宝宝按摩,宝宝会得到很多美好的激素,你自己也是,那些激素释放得越多,你们之间就越亲密。这也是为数不多能有效预防男性产后抑郁的方法之一。
值得一提的是,时不时会有一些准爸爸来求助,困惑于自己为什么没有对宝宝“一见钟情”,仅仅是理性上知道“这个小生命和我有血缘关系,我要照顾ta。”
他们会自我否定和怀疑,因为想象中——只要孩子一出生,就会立刻涌现满满爱意。在和孩子刚出生两周的爸爸们聊天时,你会发现,他们在拿自己和伴侣作比较,“她做得真好,是一个标准的好妈妈……不像我,我真的笨手笨脚。”
但事实是,这份爱意一定会来,它只是有点延迟。因为,男性是通过点滴的互动和孩子建立起亲密感的。
Steven Bartlett:可以这样理解吗?——我妻子和宝宝的感情更多是靠激素(荷尔蒙)驱动,而我的则是要通过互动?
Anna Machin:是的,因为你的激素主要是靠互动产生的,而你妻子呢,怀孕、分娩和哺乳的生理过程自带了一整套亲子激素。当然,她也会通过互动获得亲密感,但她确实走在你前面。
Steven Bartlett:看来以后得多给宝宝按摩了(笑)。
Anna Machin:你会爱上的。而且,等到孩子6个月大,你还可以尝试把「打闹玩耍」加入你们的互动之中。
男性似乎天生偏爱这类游戏。比起坐下来陪着涂涂画画,大多数爸爸会把孩子带到外面,玩举高高,互相追逐,回到屋里又一起在沙发上蹦跶,摔跤闹腾。
这种游戏的意义在于,第一,它很“身体化”,你和孩子会有很多肢体接触,很多的尖叫、欢笑,你们将同时收获多巴胺、β-内啡肽、催产素……这些化学物质会让你和孩子迅速“爱上”彼此。
第二,孩子可以学习到一些最基础的社交技能。社交的基础是“互惠”——你来我往。
而这种互惠的练习在游戏中就发生了。想一想,当我们和别人玩耍时,如果对方一点都不觉得“好玩”,你还会继续吗?你会想,我是不是玩过头了?这就是「同理心」。
只有当这种互动是平等、有来有回的,游戏才会一直有趣。
我特别喜欢的一项研究,来自一个由露思•费尔德曼(Ruth Feldman)领导的小组,她是神经科学领域的先锋人物,专门研究“亲子关系”如何在大脑层面运作。
她发现,父亲和孩子是“共同进化”的——他们天生就更倾向于和彼此一起玩耍。
无论男女,只要跟自己的孩子在一起,你的下丘脑总会分泌*催产素,尤其在温馨的互动时刻。而如果你是爸爸,这个激素的“高峰”往往出现在你和孩子一起玩的时候。
孩子也是一样——催产素的释放高峰不是来自“爸爸抱我一下”(这当然也很温暖啦),而是来自“我跟爸爸一起玩”的时候。
*催产素,光听名字,你可能会误以为它是女性独有的。并不是。实际上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“我喜欢你”、“我想靠近你”的温暖、安全和愉悦的感觉。你的宝宝、你的恋人、你的小猫小狗都可能让你分泌催产素。所以,它又名“爱的荷尔蒙”。
Steven Bartlett:那这跟妈妈是不一样的吗?
Anna Machin:有区别。
女性在照顾、尤其是拥抱孩子时,体内的催产素释放最为活跃;而小朋友也是从妈妈的拥抱中获得催产素的高峰。
说实话,我确实没有怎么研究母亲——这个领域已经有大量的研究成果。所以我现在补的是父亲这一块的空白。
我得说,在异性恋家庭中,妈妈和爸爸的角色在逐渐演化成一种互补的关系。
而无论用什么方式参与育儿,爸爸们都有一个非常关键的——这个词听起来有点技术性——叫做“支架”作用。

Anna Machin:什么意思呢?
——父亲是那个帮助孩子“从家庭走向外部世界”的人。他们会在神经连接、生理机制、心理韧性等方面,帮助孩子发育出能适应社会、走向独立的能力。
这从小朋友一出生就开始了。
我们常说的依恋关系,在母亲这里,通常是以“养育”为中心的。换句话说,孩子和爸爸妈妈之间的情感纽带,强度是一样的,但性质不同。
父亲是引导孩子“走出家门”的人。不是把孩子粗暴地推向外面,而是“我一直都在。但我要推你一把,让你出去看看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。”
与此同时,孩子的“亲社会行为”其实更受爸爸的影响。举例来说:
你可以有情绪,但你不能一生气就大喊大叫;
你可以玩,但要考虑别人;
你不总能赢,要学会输得起。
类似这样,爸爸培养的是孩子的规则感。
有趣的是,在学业成绩上,父母的影响是差不多的。但在“学习行为”这件事上,爸爸的影响更大。比如上课专注、跟同学和老师合作、不打扰别人……往往是爸爸在背后打下的基础。
Steven Bartlett:但现实是,有些爸爸就是没法经常和孩子在一起。那小朋友就没法收获这些能力?
Anna Machin:其实,极少有孩子会在生活中完全缺失“父亲”的存在。
在西方,我们都有点执着于“生物学父亲”这个说法。每次我一说“father”,大家就默认我说的是亲爹。
其实不是。我说的是那些真正承担了“父亲”角色和责任的人。
对有些人来说,那个有血缘关系的“老爸”从未出现过。手把手带大自己的,是继父、爷爷、叔叔、舅舅,甚至是哥哥。
又或者,孩子在成长路上遇到了值得尊敬、信赖的男性长辈,例如学校里的老师、教练,这些参与到ta生命中、给予了关怀、支持的男性,在社会学意义上就是父亲角色的输入。
Steven Bartlett:所以,从孩子的发展角度看,生物学父亲和比如,“照顾我长大的戴夫叔叔”之间,并没有区别?
Anna Machin:没有。因为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变化,不管你是不是孩子的生物学父亲,都会发生。它们是通过互动产生的。所以任何一个真正承担起父亲职责的男人,都会经历激素、大脑和心理上的变化。
你不会因为生了孩子,就突然拥有了当父亲的神奇能力。你是通过那些互动和付出才“成为”的父亲。
还有一个普遍的误解,大家总觉得男孩更需要“父亲”榜样,其实女孩也一样。
研究发现,那些和父亲关系亲近(心理学上称之为“*安全型依恋”)的女孩,在学业上通常表现更好,受教育程度更高,职业发展也更顺利。不仅如此,她们在成年后更有可能拥有稳定、健康的亲密关系。

Steven Bartlett:你说过,人类的大脑在育儿方面拥有惊人的可塑性?
Anna Machin:噢,对。
我们让异性恋夫妇躺到扫描仪中,然后开始播放ta们小孩的视频。
那么,我们看到的是大脑不同的区域被激活。
妈妈的是在比较原始、无意识的部分出现激活高峰——这个区域非常古老,它掌管着养育、依恋、风险识别这些关键的育儿功能。
而爸爸也会在这个脑区有一些反应,但他最活跃的区域其实是在新皮层,也就是,前额叶皮质(就在你额头后面)和眼眶前额皮质(大概在你眼睛上方)。人类社交依靠的基本就是这个区域。
它属于“意识层面的大脑”,相对比较“年轻”。这说明相比母职,父亲育儿在进化上出现得较晚,大概只有50万年的历史。
同样地,妈妈的大脑在这些区域也有一些激活,只不过没有爸爸那么强烈。
这也正好体现了,父母的角色是互补的。
但——如果养育小朋友的并不是异性恋家庭呢?大脑奇妙的可塑性来了:在没有女性参与照料的情况下,一个男同性恋爸爸的大脑会发生适应性的变化。
我们看到:除了“爸爸脑”被激活(毕竟是男性),他的大脑里,原本属于“妈妈”的那部分也被调动起来了。而且活跃的强度相当。
如果我们去看一位女同性恋妈妈的大脑,很可能也会观察到同样的变化。
Steven Bartlett:但如果两个女性也能做到这些,那是不是说明,其实不一定非得有“父亲”这个角色?
Anna Machin:不是的。
照这个逻辑,那你也可以说在男同性恋家庭里不需要“妈妈”。
我想表达的是,在异性恋家庭中,我们常常看到一种互补的照护方式。而在同志家庭里,我们看到的不是性别互补,而是大脑和行为的适应性变化。
不幸的是,目前关于同性伴侣育儿的研究还远远不够——这是个很大的空白。科学总是从异性恋出发,然后只围绕它展开研究。
所以我们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,比如在两个男性的家庭中,是不是会因为缺乏女性的参与而少了点什么;或者在两个女性的家庭中,会不会因为没有男性角色而略有缺失。这些都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。
